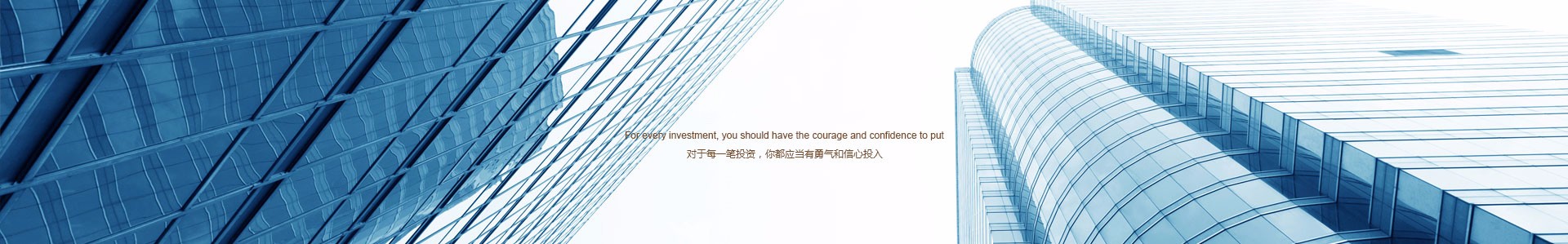金年会-官方体育与电竞娱乐平台实时赛事直播与竞猜山姆事件争议背后:阿里的黄金与铁锈
2025-11-11金年会,金年会官网,金年会登录,金年会注册,金年会app下载,在线体育投注,电竞投注平台,真人游戏平台,金年会数字站

此举震惊了当时的中国商界,两人辞职并非因为业绩不彰——恰恰相反,起因是内部调查发现,B2B团队中约100名销售,为追求业绩,纵容甚至协助了多家欺诈供应商上线。
不过在当时超过5000人的B2B团队中,这仅是少数,涉案客户占比亦不过1%。从财务角度看,对利润丰厚的B2B业务而言,实在微不足道。更何况,卫哲是马云三顾茅庐请来的明星CEO,其本人并未参与其中,仅负管理责任。
但马云的内部信措辞严厉,称之为刮骨疗毒:“这个世界不需要再多一家会挣钱的公司,但需要一家更加诚信、更加担当、更加透明的公司!” 为占比1%的欺诈案,干掉战功赫赫的CEO,阿里此举被媒体称为“壮士断腕”和“价值观标杆”。
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第一财经》等媒体都用了价值观捍卫者这样的措辞来评价马云的决策。它证明在2011年的阿里,“客户第一”的价值观不是空话,而是有人为其付出代价的底线。
今天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,当时年轻的阿里巴巴堪称中国商界的一股清流,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管理文化的新锐力量而被广泛推崇。阿里的工牌,也曾是职场上最硬的硬通货,打工人的天花板。
站在当时很难想象,十几年后的今天,当山姆会员店宣布任命前阿里高管刘鹏为中国区总裁时,却立刻激起舆论涟漪:阿里的流量打法、大数据算法,会不会将主打品质的山姆变成又一个过度内卷、去人性化管理的大厂?
我甚至看到有网友“毒舌”地评论阿里文化:“行业百草枯,职场福寿螺”。似乎无论从消费者角度,还是打工人视角,阿里都成了有毒大厂文化的代表。
实际上,早在山姆事件之前,阿里的形象标签便已在近年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中被重塑:从“996福报论”引发的群嘲,到2021年因“二选一”被处以182亿反垄断罚款,再到互联网大厂黑话被全网调侃,曾经的“价值观捍卫者”,似乎正重演屠龙少年变恶龙的剧本。
问题是,那个曾被视为中国商业文明标杆、被商界争相学习的阿里,是如何在十几年间,从箪食壶浆以迎,变成如今鬼子进村一般人人喊打的?
2000年,阿里巴巴刚成立一年,马云亲自组建了一支30人的B2B(business to business)直销团队,后来扩充到80人。这支队伍后来被誉为中国供应商直销团队,简称中供铁军。与其说这是一支销售队伍,不如说它是一场企业价值观的实验场。
马云对招聘的优先级排序极为明确:企业文化第一,价值观第一,能力第三。这不是虚言,马云曾表示,销售人员可以带来客户,也可以带走客户,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阿里巴巴的价值观,即便能带来100万元的销售收入,阿里也不要。
这支队伍的新人培训被命名为“百年大计”,简称百大,培训师是马云、关明生、彭蕾、孙彤宇这些日后的“罗汉”。百大不仅教授产品知识和销售技能,更核心的部分是三天三夜的价值观与文化浸润。这种文化第一的理念,在当时的中国企业届堪称绝无仅有。
马云挖来通用电气(GE)高管关明生加入,成为阿里巴巴从草台班子向“正规军”转变的转折点。关明生带来了GE的管理工具箱,将严格的绩效评估系统、价值观考核(GE称之为Bargain)以及精细化的运营复盘文化引入了阿里。
但仅有GE的流程是无法在当时的土壤中野蛮生长的。B2B的中国供应商产品,客单价高,客户又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外贸工厂,这些工厂老板们对互联网一无所知,因此阿里早期唯一的销售方式就是地推。
早期的中供铁军销售,被要求背着电脑包,挤着绿皮火车,住着100块的旅馆,去敲开义乌、东莞、泉州工业区里每一个工厂的大门。他们在客户门口死磕,从早上8点等到晚上8点,只为见老板一面。
这种土洋结合正是中供铁军的独特之处,它将关明生的“洋”流程与马云的“土”战术完美融合,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混合体:以GE的流程执行毛选式的动员。
那时候的阿里,还没有庞大的体系和精密的考核表。员工们信的不是KPI,而是一句写在墙上的口号——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。
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改变世界,“今天很残酷,明天更残酷,但后天很美好”,这句后来被写进无数演讲的口号,当时只是阿里办公室墙上一张手写海报。这种单纯的热血,支撑了阿里最艰难的草创期。
2011年的卫哲辞职事件,阿里为捍卫“客户第一”的价值观,不惜刮骨疗毒,干掉战功赫赫的CEO。这一刀,代价是B2B业务的短线地震,但换来的是阿里价值观的金字招牌:它向整个中国商界证明,阿里的价值观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,是需要CEO滚蛋来捍卫的红线。
现在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,2010年代,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哲学,是中国商界炙手可热的学习对象。也正是这一时期,中供铁军培养的人才开始向外输出,而这些人才,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格局。
比如创建滴滴打车的程维,2005年加入阿里B2B销售部,后来晋升为区域经理,是中供铁军最年轻的地区负责人之一。2012年,他揣着80万离职创办滴滴。这80万中,有70万来自他的天使投资人王刚——而王刚正是程维在阿里的老上司。
程维后来回忆,他之所以能在滴滴快速做出成绩,正是因为在阿里学会了如何在极压之下交付结果。当滴滴与快的合并时,投资人对程维的评价是:他身上有典型的阿里印记——对目标的执着和对过程的严苛控制。
2010年,王兴的美团在“千团大战”中苦苦撑持。王兴三顾茅庐,从阿里挖来干嘉伟,担任首席运营官。当时干嘉伟在阿里担任B2B事业群副总经理,直接管理过销售和运营。
干嘉伟到任后,利用阿里的经验,几乎是像素级复刻了“中供铁军”的地推模式——每个城市派出数百名销售、日均拜访目标客户数、团队PK机制。这支队伍,最终帮美团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,杀出了一条血路。
在中国互联网界,类似的名单还可以拉很长:赶集网COO陈国环、大众点评COO吕广渝等等,他们都是O2O(线上到线下)战场的“关键先生”。这些人才溢出,实际上是在传播一种阿里式管理哲学:目标至上、过程可视、团队PK、不计代价。
在2010年代中期,这种哲学成为了互联网打法的标准范式,而阿里人自然也成为被职场追捧的明星打工人。在那个风口起舞的年代,一个阿里P8的履历,就是VC眼中最硬的“信用背书”。阿里背景,意味着战斗力、执行力、能拿结果。挖一个阿里人,成为创业公司的标配。
这种对阿里管理哲学的追捧和自信,在2015年达到了顶峰。那一年,阿里企业文化的巅峰象征——湖畔大学,在杭州成立。
湖畔大学成立时,一度被称为商界黄埔军校,它汇聚了当时中国民营企业的顶流:柳传志、史玉柱、郭广昌、沈国军、俞敏洪等,联合创始人还包括冯仑、牛根生、刘永好等。
阿里巴巴只需要做102年就够了,湖畔大学要做300年。未来中国500强CEO中,至少200个来自湖畔大学。
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。当时阿里上市不久,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,马云风头正盛,意气风发,已经不满足于做好一家企业,而是升级到培养企业家和系统输出阿里的管理哲学。
湖畔大学的招生条件极为严苛:必须拥有30名以上员工、纳税3年以上、年营业额3000万元以上、3位推荐人(其中至少1位为指定推荐人)。这种精英筛选不仅保证了学员的质量,也强化了一种圈层文化——那些认同阿里价值观的企业家聚集在一起,互相确认彼此的管理理念。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国企业的主流是学日本。海尔的张瑞敏多次赴日,学习丰田精益生产和松下管理。那一代中国企业家的管理哲学是讲究细节、强调品质、员工忍耐。海尔“砸冰箱”的故事,就是那个时代的图腾。
到了2000年代,开始学美国。互联网泡沫破裂后,中国企业转向了GE的KPI考核制和360度评价。联想、海尔等巨头纷纷引入麦肯锡、波士顿咨询,痴迷于用量化管理优化流程。这是一个从作坊向科学管理的转变。
再到2010年代,风向又转了,开始学硅谷。字节跳动引入了OKR,互联网公司普遍学习谷歌的工程师文化和Facebook的Hacker Way——强调快速迭代、勇于试错、“完成比完美更重要”。
在这条拿来主义的演进链中,阿里的“中供铁军”模式,像一个异类。它既不像日本模式那样重“工匠”,也不像美国模式那样重KPI,更不像硅谷那样重精英。它是一种混杂了GE目标管理、中国式人情(师徒制)、军事化执行和马云个人意志的本土打法。
中供铁军培养的人才开始向外输出时,这种“本土打法”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,塑造了此后十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格局。
《左传》有云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。” 改开后崛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,在时代洪流中完成了建功立业,自然也希望有机会留下思想与言论,影响后人。如果说过去中国企业家们都在学习西方巨头的先进经验,那湖畔大学则代表了阿里第一次试图向外输出自己的经验。
那时的阿里人真心相信“客户第一、员工第二、股东第三”,可当公司规模扩张到十万级、部门成了矩阵、流程成了制度,价值观也开始逐渐从信仰变成了考核项。当文化不再是文化,而是工具,热血也就开始冷却。
2019年4月,在一次阿里内部交流活动上,马云发表了一段关于加班的讲话。这段讲话后来成为足以载入互联网史的污点记录:
能做996是修来的福报,很多公司、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。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,你什么时候可以996?……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,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。
他甚至进一步拿自己举例说:我不要说996,到今天为止,我肯定是12×12以上。……加入阿里,你要做好准备一天12个小时,否则你来阿里干什么?
这段讲话在发表后,在GitHub上迅速引发了996.icu项目,几天内获得了数十万Star。程序员们在项目中讽刺地附加了一句:在中国,996工作制的下一句是ICU。人民日报、新华社等官媒也随后发表评论,明确批评996工作制违背劳动法精神。
但更深层的伤害在于舆论心理的转变:曾经代表创业精神和奋斗精神的加班,开始被重新定义为对人的消耗和管理的冷漠。
2021年4月,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开出182.28亿元的反垄断罚单,当时流传一句网络段子:被罚182亿是一种修来的福报,很多公司想被罚都没有这个机会。
再之后,打工人眼中的阿里光环也开始褪去,代之以对大厂黑话的黑色嘲讽。被“赋能、拉齐、闭环、颗粒度”这些词充斥的语言体系,迅速从阿里内部溢出,污染了整个中国互联网的会议室。这套语言的精髓,不在于沟通,而在于包装——用最复杂的词汇,掩盖最简单的逻辑。
字节跳动的张一鸣在9周年演讲上,当众批评了一段充斥着互联网黑话的内部报告材料:我们的很多重要决策并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描述。
如果说互联网黑话是,那么361绩效考核,就是这套体系最冷酷的“发动机”。这个源自GE“活力曲线”的制度,在阿里被执行得炉火纯青:所有员工被强制按照3-6-1的比例分布:30%的优秀,60%的合格,10%是待改进或淘汰。如果连续两年处于那10%,将被直接辞退。
这个制度最险恶的地方在于:它不是一个标准,它是一个“配额”。即使一个团队所有人的表现都远超预期,他们的主管也必须硬着头皮找出那倒霉的10%——知道的人清楚这是一家公司,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这摊派“”名额呢。
它在事实上,把同事变成了零和博弈的对手。你不需要做到最好,你只需要保证自己不是最后那10%。这套系统,摧毁了中供铁军时代那种“一帮兄弟,一个传奇”的信任基础,它把人变成了KPI机器上的螺丝钉,唯一的价值就是产出数字。
这种“以效率为信仰”的文化,不只存在于会议室。它会透过员工的决策,渗入产品的逻辑里——功能越多越好、转化率越高越好、用户停留时间越长越好。
但数据背后,用户的体验、耐心和信任也在被一点点消耗。当内部管理的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,消费者感受到的,也正是那种“被运营”、“被算法”的压迫感。
这次的山姆事件,实际上,山姆在去年就因为推行激进的降本策略,选品出现了翻车,在这样的信任危机背景下,找一个阿里系高管过来,立马成了火上浇油——众所周知,阿里化意味着效率优先、数据优先、增长优先,而不是品质优先、消费者优先。
从山姆事件的舆论反应看,社会对阿里化的普遍恐惧,其实反映的是阿里管理哲学的时代错位。问题是,一个曾经把价值观和使命感奉为圭臬的组织,是如何一步步,变成一个被KPI、黑话和大企业病所异化的效率怪兽?
阿里的黄金时代(1999-2014),完美地踩在了中国增量发展的浪尖上。那时有世界工厂的崛起,有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工程师红利,有PC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人口红利。整个市场,是一个近乎无限大的蛋糕。
在增长至上的时代,996是“合理”的——因为奋斗真的等于财富。市场在高速增长,公司在高速扩张,员工的股票和奖金也在高速膨胀。你今天付出的12x12,明天就能换回一套杭州的房子。阿里P8的头衔,扔相亲市场上都一度是王炸一般的存在。
但2015年之后,中国互联网主要市场,电商、搜索、社交各个领域的人口红利基本吃尽。市场饱和,蛋糕不再变大,增长只能来自内卷——从竞争对手的盘子里,抢夺存量。当增长放缓,裁员、降薪、股价停滞成为新常态时,绩优主义和KPI高压也随之异化,996就不再是奋斗,它变成了赤裸裸的压榨。
大企业病并非阿里的专利。它几乎是所有跨国巨头,在膨胀到一定规模后,都必须面对的企业“癌症”。但不同的土壤,对此也提供了不同的药方。如果把全球的巨头企业文化拉出来看,我们会发现几个主流的范式。
第一种,是以GE、微软、亚马逊为代表的美国模式。这是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态,核心是股东价值最大化。杰克·韦尔奇在GE发明的活力曲线制”的祖师爷。这套体系的本质是职业经理人文化——一切以财务数据和季度报表为导向。它极度高效,优胜劣汰,创新动力强,但也极度冷酷、崇尚短期主义、容易导致华尔街绑架实业。
第二种,是丰田、松下为代表的日本模式。它是工匠精神的极致形态,核心是集体主义和长期主义。 丰田生产方式中的持续改善和质量圈,强调的是“自下而上”的改进。日本公司普遍品控极致、员工忠诚度高、专注“长板”。但它决策缓慢,论资排辈,组织僵化,难以适应破坏式创新。
而第三种,是以德国“隐形冠军”或北欧企业为代表的欧洲模式。这是一种“社会民主”的妥协形态,它试图在资本效率和人的价值之间找到平衡。它可持续性强,社会矛盾小,产品扎实,但在效率和规模上,根本跑不过美国同行。
那么,阿里的企业文化,到底属于哪一种?答案是:它是一个四不像的“缝合怪”。
它在内核上学习了GE的绩优主义和KPI高压,在表皮上模仿了硅谷的工程师文化和快速迭代,在执行上,又嫁接了中国本土的军事化管理和草根激情。在增量时代,这个“缝合怪”是无敌的。它拥有美国模式的效率、硅谷模式的速度和中国本土的执行力。
但在存量时代,这个缝合怪不但患上了美国模式的短期主义、硅谷的傲慢,它还患上了中国特色的大企业病。——它唯一没有的,是日本模式的长期主义和欧洲模式的人性关怀。而这,恰恰是存量时代的消费者与新一代员工,最稀缺、也最渴望的东西。
阿里巴巴曾试图通过湖畔大学来输出中国企业家的管理文化,但它在全球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。相反,一些从阿里出走的高管,在国外创业时会刻意去阿里化。这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:阿里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特色,而不是普遍适用的。它至少依赖于以下几点:
一旦这些条件改变,比如人口老龄化、监管收紧、劳动意识提升、消费者审美升级,这个模式就开始失效。换句话说,阿里形象的变化轨迹,或许主因并不是企业内部因素,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变化的映照。
企业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,它必须随着社会条件而演进。当整个社会开始从追求增长向追求质量转变,“高效率、低成本、大规模的管理模式开始失效,而人性化、品质化、可持续的模式才能获得青睐。
吉姆·柯林斯(Jim Collins)在《基业长青》写道:“伟大的公司并不是永远伟大,只是暂时幸运。”
马云曾说,阿里巴巴要活102年,因为那样才能横跨三个世纪。但跨越时间,可能比跨越周期更难。互联网世界的生命周期,往往只有十年,所谓风口浪尖,往往转瞬即逝。在一个急遽变化的世界,坚守与耐心成为最稀缺的东西。
这不是阿里一家的宿命,而是所有伟大企业的必经阶段。今天的世界500强企业,大约只有80家有百年以上的历史,绝大部分公司注定消逝在历史的长河。
据说很多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大佬都喜欢刘慈欣的《三体》,喜欢用“黑暗森林”、“降维打击”形容商业竞争,硬是将科幻隐喻,讲成了互联网黑话。
这难免让人想到,在面临极度内卷时,他们是否也会毫不犹豫地认同维德那句“失去人性,失去很多;失去,失去一切”。
但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事实是,无论企业员工,还是他们服务的消费者,都并不是小说中地球人类的死敌“三体人”,而是每个商业帝国的基石。
而同样作为三体迷,我更喜欢《三体》第三部中,当人类面临末日打击,尝试破解云天明的童话谜团时,一位百岁老人讲出的那句意味隽永、而又充满宿命感的台词:“一切都会逝去,只有死神永生。”
现实的商业世界,当然不会像刘慈欣笔下的宇宙那般冷酷,但对于历史尚不算长的中国企业来说,能否在时间的考验中保持初心与生命力,肯定不只是阿里一家要面对的命题。
[5] 虎嗅网. 阿里史上最强人事地震回顾:中供铁军何以被生生解体. (2018-04-08)